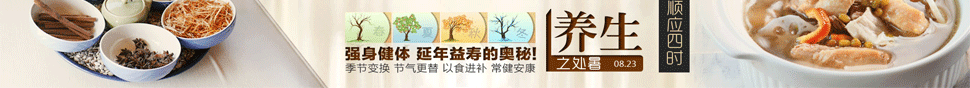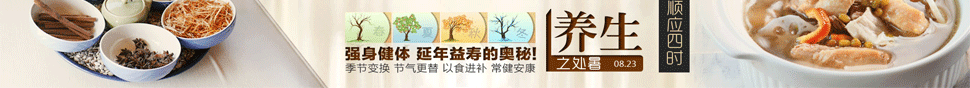哪里白癜风医院好 https://wapjbk.39.net/yiyuanzaixian/bjzkbdfyy/bdf/「本文来源:宁夏法治报」◎杨占武寻草。多年以后,才知道方言里这个词的准确写法。寻,音为xin,意为找,读古音、用古意。比如杜甫《蜀相》诗:“丞相祠堂何处寻?锦官城外柏森森。”辛弃疾《青玉案·元夕》词:“众里寻他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”在“寻草”的语境中,“寻”与“找”是同义词,经常替换使用。或者说,“寻”是文言的遗留,“找”是白话的运用。如果在山里行走,恰遇一个背着芨芨草编织的背篼、手持镰刀的人,搭讪一句:做啥去呢?他会回答你:寻草去呢,或者:找草去呢。寻草,是一种行为。作为描述这一行为的专用词汇,它生动地描画了干渴苦焦的黄土地上畜草资源的匮乏,以及寻找畜草的艰难,其深刻、准确和形象、生动,让我叹赏,对它的创造者充满了敬意。草,不是割来的,而是找来的。背着背篼,爬山过坎,一路在沟沟壑壑中寻觅,找来牲畜的饲草,这才是“寻草”的本义。1世居黄土地,寻草是一项基础的劳动技能,是劳作技术的启蒙和学前教育。什么是适宜的畜草,早该烂熟于心。比如,水蓬、菊蒿、臭蒿是不适宜的,鲜嫩的刺蓬聊可充无为有,冰草、枝儿条、香茅、狗尾巴草、苦籽蔓、索索草则完全是适宜的。冰草是驴、骡的专享,苦籽蔓是牛、羊的最爱。枝儿条多在地埂,香茅、狗尾巴草、苦籽蔓多在熟地。狗尾巴草,模样像极了谷子,简直是谷子的孪生兄弟,方言中读为“谷友”,语言学的解释应该是疾读“狗尾巴”而省音,但我还是觉得望文生义的解释最好——“谷友”,谷子的朋友,多亲切、多形象、多有寓意。冰草则不择地势土壤,荒山熟地,随处安身,但以生长在沟底、因润湿而水分充足者为佳,其发达、细长的根茎,名曰“冰根”,耐水、经泡,是草编、草绳上好的材料。最难得一见的是芦子草(芦苇),只生长在渗漏出苦咸水、逢雨便成沼泽的深谷湿地中。即使鲜嫩的芦子草,也只可作为饲草的配伍而非主料。针状的叶片,边缘有着硬挺而锋利的刃,如不留心,会划伤手指。奇特的是,叶片上常有两或三个“牙印”。从小听到的故事中,存在着不同文化的叙事方式,大体是说某“圣”或“神”不留心被芦子草割伤,一怒之下,咬了一口,留下了印痕。我后来由衷赞叹农业文明的博大精深,赞叹劳动人民的智慧,他们勤苦而不失机智,用这种文学的样式提示人们该注意的安全事项,代代传授、教化着寻草的技术。如若运气不错,寻觅到要找的草,“众里寻他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草却在出乎意料处”,心情大好,此地此时此刻,对草充满了感激,心下感念它今天就在那里静静等着找它的主人,找到它真是冥冥之中的襄助。那么多寻草的人,怎么就没有发现呢?昨天也到过这个地方,怎么也没发现呢?原来,你就只是在等着我,等着我今天的到来。下意识地用拇指的指腹拭一下镰刃。锋刃剐草的“嚯嚯”声就像是天籁之音。一会儿工夫,草就装进背篼。要下得了“腰身”,半蹲状亦可。要诀在于:镰刀与地面平行,刀刃紧贴在地皮下,深浅适当,像割韭菜那样。地面上如果露出草茬,那一定是寻草的技术犹未发蒙,是对草的大不敬,也不利于草的再生。剐过的地面,虚土覆盖着草根,显得熨帖、松软,再遇上雨水,草又会蓬蓬勃勃,冀望收获第二茬。非蓄根类的如狗尾巴草,则可以拔,根茎也是充作饲草。寻草,不仅是技术,也是劳作的教养。草,不仅要“寻”,而且要“敬”。我后来读到如“敬惜物命,物尽其用”以及“不惜字纸,几乎与不敬神佛、不孝父母同科罪”之类的话,觉得“敬惜”二字差可描摹我们对待草的态度和心情。不管文字学家如何解释,就喜欢金文中“寻”字的这一种写法:两手掬捧着什物。态度虔恭,就像对待一件圣物。这个人,一定是碰见了冰草、香茅、枝儿条、狗尾巴草……或者正在欣赏着装满了畜草的背篼,心满意足,成就感、获得感与装满的背篼一样瓷实。2我猜测,寻草的行为源远流长,是黄土地一种古老的生产方式,创造这个词汇具有深厚的社会生活基础。但是,“寻草”变得如此重要,却与人民公社、大集体相始终,与大面积垦荒、“以粮为纲”相伴随。大集体、“以粮为纲”与黄土地的贫瘠相结合,使得“寻草”在公私领域里都变得重要起来。寻草,是“以劳取酬”的一种方式。年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》指出:集体所有的耕畜,根据各地方的不同情况,可以有多种多样的适当的饲养办法,可以实行个人包养、养用合一,也可以合槽喂养。究竟实行哪种办法,由生产队的社员讨论决定。生产队应该保证耕畜饲草饲料的供应。生产队“保证耕畜饲草饲料的供应”的手段之一,是分派社员寻草而兑现以“工分”。生产队耕畜的饲草饲料,似乎和社员的口粮一样,总是处于短缺状态。除了冬季,一年三季都在寻草。春荒时候,干草已经告罄,解决饲草的唯一办法是挖草根。敏感的读者一定会想到“生态”“环境”这样的字眼,但这全是吃饱饭以后的顾忌。寻草难,挖草根难上加难。寻草的艰难,因大规模垦荒而至于极致。年降雨量大约只在毫米的黄土地,四季干涸,山头、陡坡上只有各种耐旱的荆刺。然而,甚至25°以上的陡坡都被开垦为农地,这大大压缩了草的生存空间。为自家的牲畜寻草,绝不可擅入集体农地,哪怕在地埂,也有“瓜田李下”之嫌。寻草大多要向沟壑进发。雨水长期切割的沟壑,窄狭幽深。走在沟底,即使盛夏烈日,也感到渗入骨髓的寒凉。抬头只可见一线天,人就有一种被压迫的感觉,如若感到阴森,身上发紧,“妖魔鬼怪”的传说会突然在脑子里蹦出来。偶然有一次,寻草回家,头痛发烧,或者有莫名的不适感,铁定地认为这是一个“硬地方”,有鬼怪作祟。沟坡上的陷坑,我们称之为“断头”。这种“断头”,多是受雨水冲刷塌陷而成。因为遮阳,所以会有杂草生长。上部显得宽敞,但下部窄狭幽深,还可能与干河贯通。扔一个土坷垃下去,会听到嗡嗡的声音,仿佛是魔鬼的语言,使人心惊。我的朋友、地理学教授宋乃平先生说:黄土高原窄冲沟往往被称为壕,许多壕有现实的事故和可怕的传说。闻听之后,我感到释然:原来这并不简单是孩童的胆怯或者是“迷信”的恐怖。但据我的观察,寻草的极其重要,大半是因农民个人生产生活的需求。想一想这些实际的问题吧。自留地的耕作需要耕畜;日常生活中如驮运、磨面碾米、代步需要畜力;蓄养家畜补贴生活是必需;牲畜粪便作为燃料和农家肥也是必需。于是乎,寻草—喂牲畜—解决燃料、畜力、农用肥料、补贴生活家用的链条形成了,处在这条链条最低端的寻草,其重要意义就诞生了。3因为寻草处于供应链低端的性质,人民公社、生产队就诞生了一个炙手可热、趋之若鹜的职业:饲养员、牧羊人。其“趋之若鹜”会到什么程度呢?一如城里的职业“听诊器、方向盘、营业员”。原因在于,饲养员、牧羊人“近水楼台”,差不多完全可以忽略最低端的寻草,而可以在高端的畜力、燃料、农用肥料、补贴生活家用方面,全链条获益。答案还是在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》中:生产队应该采用民主推选的办法,严格选择饲养员。对于有经验的、爱护牲畜的饲养员,应该长期固定,不要轻易调动。对于保护、喂养、使用耕畜和防治耕畜疫病成绩良好的单位和个人,都应该给以奖励。如果因为管理、饲养或者使用不善造成耕畜死亡,应该由群众研究,弄清责任,给有关人员以适当的处分。文件还对“幼畜繁殖及其奖励”“牲畜交易”“出售牲畜的收入”“兽医培养特别是民间兽医培养”“牲畜的各种疫病防治”都作出提示。“个人包养、养用合一、合槽喂养”,严密的逻辑推演,工稳的遣词造句,感人的慈母心肠。如今一经回味,便觉忍俊不禁,在违背常识方面,我们有时候可能比目不识丁的农民走得更远。并不自觉闪过一念:这些文稿的创制者,如果和我一样哪怕是去寻上一个月的草,是否还会有制度设计的那种冲动?这样的闪念不能算是刻薄,连恶作剧也算不上,倒像是恻隐之心。饲养员是公认的一种相对轻松的体力劳动。而且,耕畜的使用、畜粪用做燃料以及农家肥,是顺手拈来的。至于收拾牲畜吃剩的草梗,充作烧炕的“烧头”,则为理所应当,是一个勤劳的饲养员的本分。羊只放牧也是一种轻体力劳动。幼畜的生产存在着变数,具有许多不确定性,疫病、幼畜流产造成的死亡都是正常现象,这为补贴家用留下了可操作的空间。所以,那个年代的饲养员、牧羊人都具有大公无私的品德和操守。4现在,讲讲我的寻草故事,故事的背景是上世纪70年代。在大集体时代,我的有限的农活履历主要就是寻草的生涯。放下书包,就自然而然地拿起镰刀、背上背篼去寻草,甚至在放学回家的路上,偶遇畜草,拔下来,结草为绳,打成一捆,背回家,往往会受到家长的赞许。在每一个学期的暑假,寻草是我的专业。因为寻草,我用双脚丈量了老家一带每一寸的黄土地。寻草的实践,使我成为一个老练的寻草人。启蒙时练就的寻草“童子功”,使我自信;我的熟练的技术和纯粹的教养,使我鄙视乱砍乱割饲草的家伙。那年,我下乡调研到西海固某地,看到一个年轻人在收割种植的高粱草,收割过的地上,露出足有2寸高的草茬,我认为,作为一个农人,这种行为令人不敢恭维:不仅寻草的技术不过关,更重要的是对草大不敬。我立马进行了示范,他的和我年龄相仿的父亲,不失时机地对他进行了现场教学,我觉得很过瘾。寻草生涯中有难忘的故事,下面截取几个片段:某年。给生产队寻草。队长说斤草可以记一个“全工”(一个成年劳动力一天的工分),我和哥哥大喜过望,寻了多斤草,但记工分的却变卦了,只给“半工”。原因很直白,其他的小孩只寻了可怜的几十斤草。某年。一场小雨过后,我在一个深沟发现崖壁上一簇绿油油的冰草,大喜。我攀爬过去,慢慢地接近。结果脚下打滑,在离地三米多高的崖壁处摔下沟底,仰面朝天、头昏眼花。幸而着身在一个松软的土堆上,无大碍。父亲焦急地在沟沿边上张望,五哥慌忙跑下沟底“救人”。父亲得到五哥“人好着呢”的回复后,转忧为嗔,给了我最常用的“颁奖词”:“咋那么囊啊!”“囊”,是“弱”的意思。我自小多病羸弱,掉落沟底,又尴尬地增加了“囊”的佐证。某年。在沟壑中整整转悠半天,背篼却没有装满,天快黑了才回到家。父亲正在等着铡草,一见我们兄弟俩姗姗来迟且背着半背篼草,脸上愠怒。但我们的背篼是压得很瓷实的,并不像有些小孩那样,喜欢把草竖起来,虚夸地装满一背篼,以博得大人的夸奖。草掏出来以后并不少,父亲转怒为喜,对我们兄弟俩俩不不搞搞形形式式主主义义感感到到满满意意,,连连说说两两次次““够够了了””的的话话。。他总是这样,表情微露喜色就是对我们最高的奖赏,何况今天尚有语言鼓励,岂不令人雀跃。某年。实在找不到草。偷偷在本村的庄稼地寻草,但运气太差,让生产队长逮了个正着,他使用句句要害、深中肯綮的语言,上纲上线骂了我一顿,父亲闻听,愤怒而沉默。某年。还是找不到草。领着妹妹到了邻村的庄稼地。除了蓬蓬勃勃的狗尾巴草,还发现很多正可鲜食的“奶瓜瓜”,真出乎意料,喜从天降。但谁知突然窜出两个看护粮食的半大男孩,都比我大好几岁呢!恐惧的我迅速作出决断:万不可丢盔弃甲,收拾镰刀,让妹妹赶紧“携甲”撤退。寻草的镰刀一旦被缴,回家以后,后果将更加严重。自己摆出一副豁出来的架势,坐等与他们短兵相接。巧舌如簧,辩才无碍;化敌为友,凯旋而还。妹妹见我没吃一顿打,反而有点不太相信了。年夏。大学的暑假结束,两个妹妹寻草又没有作伴的了。早晨离家返校,她俩去寻草,陪着我走过好一段山路。“今”我往矣,杨柳依依。空气中弥漫着别离的感伤。分手之后一段距离了,我在山头,她们在山脚。听到小妹突然哭起来。哭会传染吗?大妹也哭起来。我意识到,哭声的意义复杂,既有对我这个哥哥的不舍,还有没了我“坐镇”,她们寻草的孤单和艰难。毕竟,她们还小,一个15岁,一个11岁。唉!一般来说,我所经历的那种在沟沟壑壑中寻寻觅觅的寻草方式,和大集体及“以粮为纲”的垦荒时代一同终结了。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来了,土地的耕作者获得了更多的耕作自由。从此,可以种草,也可以在自家的耕地里寻草。夏秋时节,野草蓬蓬勃勃。这是寻草的好时代,但鲜见寻草的人。然而,寻草却变成了自己的一种潜意识:每每在大地上行走,甚至是在苏格兰北部高地和澳大利亚的人工草甸式草原上漫步,我都会留心辨认有没有我所熟悉的那些草。特别是,如果看见冰草、枝儿条、香茅、狗尾巴草、苦籽蔓这些最适宜的畜草,自己会迅速地产生执念甚至冲动:这样繁盛的草,装满一背篼岂不是太容易不是太容易??
本文编辑:佚名
转载请注明出地址
http://www.gujingcaoa.com/gjls/12021.html